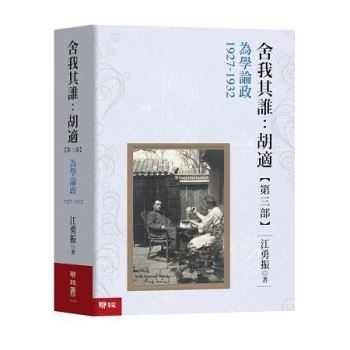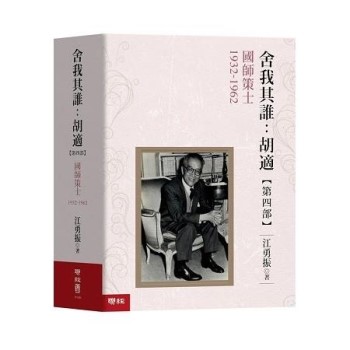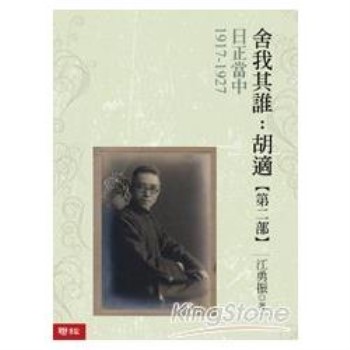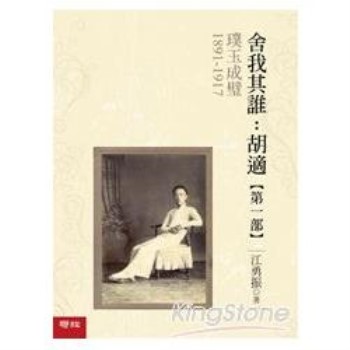-
排序
- 圖片
- 條列
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
胡適認為: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和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。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;另一方面,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,他說,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,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,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、領政的偉大。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,他在《新月》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,其實是「閻王好惹、小鬼難纏」的精彩戲碼。然而,這個時候的他,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。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,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。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,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。他說,日本是現代化其表,而封建其實。反之,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,其實是最徹底的。在另一方面,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。他說中國思想史,只是一部寒傖史。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《中國哲學史》的全卷。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、刺蝟心的矛盾以外,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,以及他在抗戰、冷戰時期的曲筆。更重要的是,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,已經味同嚼蠟,索然無味。
舍我其誰:胡適,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
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》。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階段,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《國師策士》是四部曲的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完結篇。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: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、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,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。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。他們之間的不同,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,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;胡適則明白宣示他「苦撐待變」的真諦,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,以便一舉反攻大陸,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。胡適的反共,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,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、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。晚年的胡適不是「自由主義者」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。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「新保守主義者」。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,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「新保守主義」。
【電子書】舍我其誰:胡適,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
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》。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階段,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《國師策士》是四部曲的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完結篇。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: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、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,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。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。他們之間的不同,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,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;胡適則明白宣示他「苦撐待變」的真諦,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,以便一舉反攻大陸,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。胡適的反共,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,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、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。晚年的胡適不是「自由主義者」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。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「新保守主義者」。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,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「新保守主義」。
【電子書】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
胡適認為: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和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。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;另一方面,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,他說,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,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,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、領政的偉大。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,他在《新月》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,其實是「閻王好惹、小鬼難纏」的精彩戲碼。然而,這個時候的他,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。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,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。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,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。他說,日本是現代化其表,而封建其實。反之,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,其實是最徹底的。在另一方面,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。他說中國思想史,只是一部寒傖史。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《中國哲學史》的全卷。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、刺蝟心的矛盾以外,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,以及他在抗戰、冷戰時期的曲筆。更重要的是,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,已經味同嚼蠟,索然無味。
【電子書】【舍我其誰:胡適】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
胡適認為: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和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。 1927至193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提出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;另一方面,他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,他說,中國思想史,其實只是一部寒傖史。 胡適在1926到1927年歐遊期間,患了法西斯主義急驚風,禮讚國民黨以黨統軍、領政的偉大。這個急驚風退燒以後,他在《新月》雜誌上演了一齣看似單挑國民黨,其實是「閻王好惹、小鬼難纏」的精彩戲碼。然而,這個時候的他,已經開始走近蔣介石。他在1930年底回到北大,從事北大中興的工作。從這個時候開始到1930年代中期,是胡適在思想上變化極大的一個階段。一方面,他比較中日兩國的現代化,提出了中國比日本更為現代化的奇論。他說,日本是現代化其表,而封建其實。反之,中國的現代化看似迂迴遲緩,其實是最徹底的。在另一方面,當時的胡適對中國歷史傳統的評價極為負面。他說中國思想史,只是一部寒傖史。胡適一生當中沒有完成他的《中國哲學史》的全卷。其原因除了他狐狸才、刺蝟心的矛盾以外,還有他1920年代在中國哲學史詮釋上所產生的一個斷層,以及他在抗戰、冷戰時期的曲筆。更重要的是,中國思想史對晚年的胡適而言,已經味同嚼蠟,索然無味。
【電子書】【舍我其誰:胡適】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
胡適與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繼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一部:璞玉成璧,1891-191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二部:日正當中,1917-1927》、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三部:為學論政,1927-1932》後,江勇振教授推出《舍我其誰:胡適,第四部:國師策士,1932-1962》。 1932至1962年這段期間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階段,胡適跟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,但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《國師策士》是四部曲的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完結篇。 這部完結篇所分析的,是胡適一生當中最被人誤解、不解與亂解的幾個階段:包括他1930年代的政治學術思想、擔任中國駐美大使時期的言論與作為,以及從國共內戰到蔣介石敗走台灣以後的所作所為。 胡適和蔣介石同道相謀反共。他們之間的不同,是蔣介石心知要反攻大陸就必須靠美國,但在嘴巴上就是不肯承認;胡適則明白宣示他「苦撐待變」的真諦,是在等待美國發動全球性的反共聖戰,以便一舉反攻大陸,甚至直搗國際共產的老巢莫斯科。胡適的反共,比蔣介石更為徹底和極端。 胡適不但是美國思想脈絡之下的冷戰鬥士,他更是美國冷戰鬥士裡的冷戰鬥士、美國冷戰鬥士的鷹派裡的鷹派。晚年的胡適不是「自由主義者」這個籠統的字眼所能形容的。他是美國脈絡之下的「新保守主義者」。這種保守主義不是西方傳統的保守主義,而是以確保美國霸權為宗旨的「新保守主義」。
日正當中 1917-1927【舍我其誰:胡適第二部】
胡適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胡適保存的日記和信件,讓研究他的人如入寶山 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第一部是《璞玉成璧 1891-1917》 《日正當中 1917-1927》是第二部 從胡適1917年,到1927年 可說是胡適如日中天的黃金十年 當前胡適研究最大的一個盲點,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資料出現的情況之下,才可能會有胡適研究的新典範出現。江勇振認為,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、要開創出新的典範,新的觀點才是法門。 日正當中 1917-1927從胡適進北大開始,到進入杜威和赫胥黎的思想世界,如何過關斬將,爭文化霸權,到胡適的及時行樂觀等等,都有極為細膩的觀察與描述。
【電子書】日正當中1917-1927【舍我其誰:胡適第二部】
胡適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胡適保存的日記和信件,讓研究他的人如入寶山 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第一部是《璞玉成璧 1891-1917》 《日正當中 1917-1927》是第二部 從胡適1917年,到1927年 可說是胡適如日中天的黃金十年 當前胡適研究最大的一個盲點,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資料出現的情況之下,才可能會有胡適研究的新典範出現。江勇振認為,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、要開創出新的典範,新的觀點才是法門。 日正當中 1917-1927從胡適進北大開始,到進入杜威和赫胥黎的思想世界,如何過關斬將,爭文化霸權,到胡適的及時行樂觀等等,都有極為細膩的觀察與描述。
【電子書】日正當中1917-1927
胡適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胡適保存的日記和信件,讓研究他的人如入寶山 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系列的第一部是《璞玉成璧 1891-1917》 《日正當中 1917-1927》是第二部 從胡適1917年,到1927年 可說是胡適如日中天的黃金十年 當前胡適研究最大的一個盲點,就是迷信只有在新資料出現的情況之下,才可能會有胡適研究的新典範出現。江勇振認為,要突破當前胡適研究的瓶頸、要開創出新的典範,新的觀點才是法門。 日正當中 1917-1927從胡適進北大開始,到進入杜威和赫胥黎的思想世界,如何過關斬將,爭文化霸權,到胡適的及時行樂觀等等,都有極為細膩的觀察與描述。
【電子書】璞玉成璧【舍我其誰:胡適第一部】
胡適這位超級名人,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無數的人想要窺探他 也有無數的人誤解他 《璞玉成璧》 是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這套傳記五部中的第一部 從胡適1891年出生,細數到1917年他學成歸國 本套書是胡適研究者的寶書 保存了幾乎所有的日記、回憶和信件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、範圍最廣,自傳、傳記資料收藏最豐的一個名人;同時,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,最被人顧盼、窺伺、又最被人所誤解的一個名人。他最對外公開,可是又最嚴守他個人的隱私。他所蒐集、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、回憶、以及來往信件,其實等於是已經是由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,是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所先打好了的一個模本。 面對胡適的這個傳記模本,研究者必須要能取其所用,而不為其所制;要能不落入那「浮士德式的交易」的窠臼;要能不為了換取些許資料,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。換句話說,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,得其寶,而且能全身而出,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。
【電子書】舍我其誰:胡適(第一部)-璞玉成璧.1891-1917
胡適這位超級名人,是近代史上的閃耀巨星 無數的人想要窺探他 也有無數的人誤解他 《璞玉成璧》 是《舍我其誰:胡適》這套傳記五部中的第一部 從胡適1891年出生,細數到1917年他學成歸國 本套書是胡適研究者的寶書 保存了幾乎所有的日記、回憶和信件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著述最多、範圍最廣,自傳、傳記資料收藏最豐的一個名人;同時,他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,最被人顧盼、窺伺、又最被人所誤解的一個名人。他最對外公開,可是又最嚴守他個人的隱私。他所蒐集、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、回憶、以及來往信件,其實等於是已經是由他篩選過後的自傳檔案,是他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所先打好了的一個模本。 面對胡適的這個傳記模本,研究者必須要能取其所用,而不為其所制;要能不落入那「浮士德式的交易」的窠臼;要能不為了換取些許資料,卻賠去了自己的靈魂。換句話說,研究者必須要能入胡適的寶山,得其寶,而且能全身而出,不被寶山主人收編為其推銷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