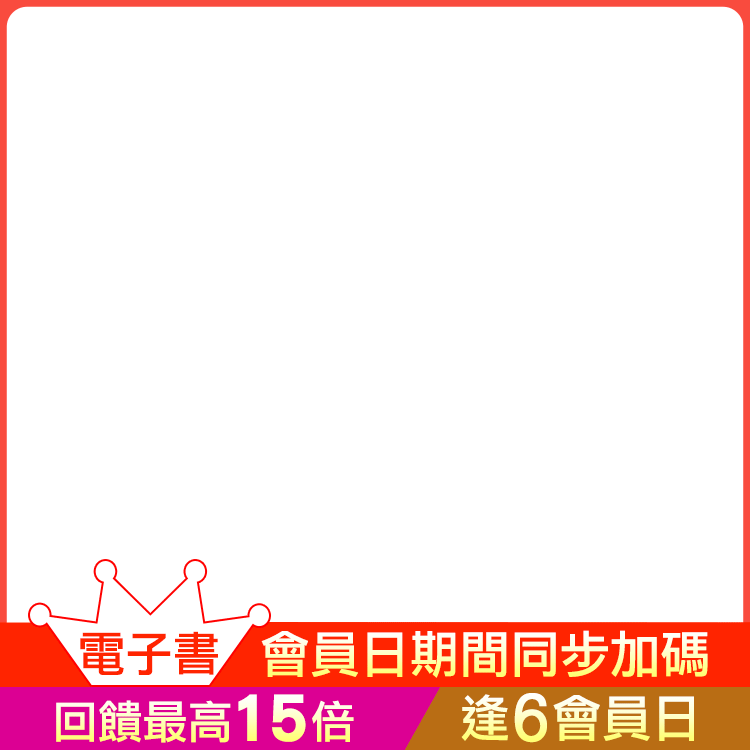-
排序
- 圖片
- 條列
後街:一部來自新疆的小說
宛如卡繆《異鄉人》與卡夫卡《城堡》當代最重要的維吾爾族作家之一,帕爾哈提.吐爾遜透過數字、性與氣味的隱喻,漫遊在濃霧的城市中孤獨、無奈、異化,作為一個維吾爾人,哪裡有我的位置?我相信沒有最終的真理。而且我相信精神疾病一直都存在。大部分情況下,它存在於各種形式的「正常」中。事實上,不符規範的人才是心理最健康的人。自認正常的人其實遠較為瘋狂。我喜歡描述特定時空下的奇怪個體,藉以顯示主流社會到底有多不正常。──帕爾哈提.吐爾遜 「在這座陌生城市裡,我不認識任何人,所以不可能與任何人為友或為敵。」這是小說當中不斷重複出現的句子,反映了主人公與城市疏離的關係,同時也像是一種宣告。 主人公漫遊在充滿濃濃大霧的城市之中,尋找著屬於他的棲身之所。在辦公室裡,他唯一擁有的是一個無法上鎖的抽屜,帶著狡詐笑容的上司逮到機會就要刁難他,質疑這個試用期間的維吾爾人夠不夠格,不肯給他分配一個棺材大小的宿舍。在北京上學時,他與其他同鄉擠在一塊,不認識其他人,生活空間只有教室、宿舍、食堂與圖書館,對首都的認識比在遙遠鄉村時透過照片看到的還要少。在童年的南疆農村,他的回憶有鄰居女兒甜美的氣味,以及父親醉醺醺的酒味;有初戀的悸動、母親的關愛,也有家庭暴力的恐懼。 小說場景在烏魯木齊、北京、童年的農村間不斷切換,沒有一處是主人公的安身之所,到哪裡都格格不入,他就像城市中到處被驅趕的鼠輩──「牠們生活的全部內容就是進食、睡覺和生育,似乎也跟城裡人的生活差不多。那些我們甚至不願想像且令人作嘔的生物,正偷偷享受進食、睡覺和生育──犯下活著的神聖罪行。」 相對於主人公的一無所有,「有些人甚至不滿足於坐擁自家土地、宮殿與豪宅,而欲將整個城市、國家和宇宙本身據為己有。」只有「數字」是他可以託付的,偶然間掠過他眼前的數字,彷彿都是指引迷途的暗語。「在許多人眼中,數字的書寫既不押韻也不講理,因此毫無意義。但我的想法恰好相反。我一向認為只有數字才能真正具有意義。」他不斷在濃霧之中尋找那個數字所對應的門牌號碼──在故事的結尾,他終於抵達了「那個地方」。